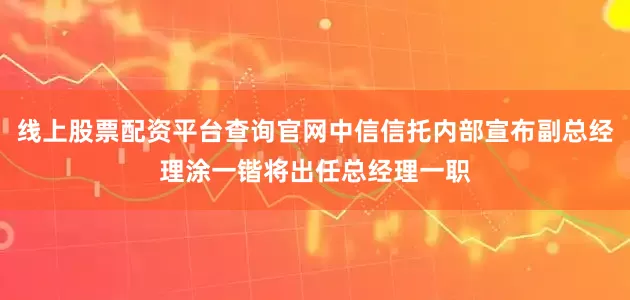有时候真的觉得,命运这东西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8月12号江西一个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了条消息,说自己的同学走了,才39岁,后来才知道其实是38岁,这个人叫张为艳,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微生物学博士,宁波大学医院部特聘副研究员。说实话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是有点震惊的,38岁啊,正是人生最好的时候,博士学历副研究员职位,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从她同学晒出的照片来看,张为艳长得挺优雅的,而且竟然不是近视眼,这在高学历人群里真的挺少见的,想来家庭条件应该不错,她父亲原本就是小学老师,在江西某所小学教书,后来调到方村小学张为艳就跟着过去读书了。
展开剩余79%在父亲的影响下张为艳从小成绩就特别好,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学一路都是优秀学生,到了浙大之后更是厉害,多次拿一等奖学金参与各种科研项目,从国家重大项目到地方性自然科学基金都有涉及,还有好几个发明专利虽然是和别人合作完成的但能力确实没话说。
可是这样一个优秀的人最终还是败给了病魔。
宁波大学医学部官方账号发了篇为她筹款的文章,从里面可以看出张为艳确实去世了,死因是低位直肠腺癌并肝转移,和病魔斗争了一年多最终还是没能挺过来,留下了两个年幼的孩子和一个待业的老公,说到这里就更让人心疼了,治疗期间每个月要两万块的自费治疗费,就算是博士工资也撑不住这样的开销啊,学校虽然组织了筹款但杯水车薪真的只能缓解一时的压力。
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在想,搞生物研究的人天天和各种微生物打交道会不会职业风险比较高?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张为艳的病和她的工作有直接关系,但这种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吧,毕竟每个职业都有自己的风险科研人员接触的东西普通人接触不到危险系数确实可能更高一些。
这让我想起前几天刚刚发生的另一件事,浙大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35岁的特聘副研究员杜老师,8月4号从高空坠落身亡,这个杜老师也是个人才浙工大本科浙大农业工程博士2020年留校任教,短短五年时间从学生变成了博导研究果蔬采收机器人什么的,典型的寒门逆袭,但就是这样一个前途无量的年轻学者却选择了这样的方式结束生命。
有人说是因为考核没过有人说是感情问题,但具体原因校方也不愿意多说只是回应"暂不对外",工会那边更是说"暑期不便回答"好像一条生命的消逝就是件小事似的,其实想想也是现在的高校考核制度确实挺残酷的,"非升即走"让多少年轻学者压力山大,虽然杜老师还没到考核期但35岁是申请基金的年龄红线这个压力估计也不小。
在学术圈里失败好像是种传染病没人敢承认自己撑不住了。
两个案例放在一起看真的让人感慨,高学历群体看起来光鲜亮丽实际上承受的压力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农民种地虽然辛苦但心里踏实,学者们顶着博士博导的光环却可能活得像知识佃农随时面临着各种考核压力,张为艳和杜老师的悲剧其实反映的是整个学术体制的问题。
冷门学科的研究者被迫去追热点,教学贡献在考核中权重几乎为零国家级课题申请卡死35岁门槛而现在博士毕业普遍都超过30岁了,更要命的是心理问题还被污名化"非升即走"失败了连个体面退场的机会都没有,我们的教育能培养出解决技术难题的科学家却教不会他们怎么和这个世界和解,985高校的实验室里堆满了精密仪器却放不下一张让人放松的椅子。
也许真的该给青年教师减减压了延长考核周期设立教学型职称通道,把心理咨询纳入教师福利定期筛查心理状态,别让天台成了最后的避难所别让实验室成了生命的终点。
科研本来应该是探索未知的乐趣,不应该成为压垮生命的稻草。
发布于:江苏省专业网上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